文 / 王斐蘊
- 20世紀重要攝影師布拉瑟(上):我在尋找詩意,世紀瑟下像是重攝改變人的霧、改變城市的影師藝術夜
藏身夜晚的人物
對布拉瑟(Brassaï)來說,夜的布拉必吸引力不只在美學的啟示,更展示在夜裡活動的記錄家作家和人身上。黑夜使人靜澱,誤入也讓城市脫卸白晝冠冕堂皇的歧途面具:夜晚驅離仕紳階級,形形色色的壞蛋都庶民日常和遊走道德邊緣的地下世界才現身展開熱烈活動。
布拉瑟幾乎囊括了整個支撐正式與非正式經濟活動的世紀瑟下底層社會,在《夜巴黎》與《三十年代的重攝秘密巴黎》裡,雖然也呈現高級時裝晚宴的影師藝術霓裳鬢影和踏入克里昂旅店(Hôtel de Crillon)和歌劇院的貴族,但更引人注意的布拉必是浮華如夢的夜總會女郎群像,酒吧裡變裝狂歡的記錄家作家和同志。
還有勞動者:斗篷在疾駛的誤入自行車上鼓脹如鴿翼的值夜警察,巴黎中央市場的歧途(Les Halles)將郊區的蔬菜肉品運到城市卸貨的攤販,拋光電車軌的工人、汙水池清潔工、麵包師、印刷工、熄燈人等等, 布拉瑟將他們從平凡和遺忘打撈出來,一一化為令人難忘的身影。
 Photo Credit: Paris.© Brassaï Estate,截圖自漫遊藝術史
Photo Credit: Paris.© Brassaï Estate,截圖自漫遊藝術史對於底層社會,布拉瑟有著和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一樣的熱情,他們對禮教法紀的不屑一顧總令他覺得自己在他們面前矮了一截,他洞悉真正的夜貓子並不見得出於生計,而是出於想要藏身在夜晚的慾望。他們屬於一個愛恨情仇、擺脫不了罪惡和毒品的世界、一個封閉、神秘、自成一格的社會。
在所有大城市中,都有一些區域只在黃昏之後才能展現出自己的特質。此時此地的巴黎透露它最不為人知,卻也最生猛的真實,恍若幾世紀以來傳嬗下來遙遠的民謠傳奇,沉澱在人的記憶深處,讓布拉瑟以朦朧的氛圍召喚出來。
瞭解,同理,不帶批判
布拉瑟將他遇到的各種角色稱為「類型」,的確他所呈現出來各種人物肖像似乎緊密吻合觀者想像,近逼原型或象徵。但布拉瑟是如此善用隱喻、暗示,使類型也生出鮮活的性情和情緒渲染力。
摩天輪中忘我親吻的情侶,被拋擲到高空的身軀一如心旌蕩漾,是以景喻情的佳例;街角站壁的妓女不苟言笑的嘴唇似乎拒絕親吻,給路人的唯一暗示是淡淡的睫毛閃爍,那樣冷硬挑釁的眼神只有在險惡街頭討生活的人臉上才看得到;黑幫份子則是不怕衝突的狠腳色,眼神和口袋裡的刀槍同樣具有殺傷力;被布拉瑟暱稱「珠寶」(Bijou),徘徊在蒙馬特咖啡館的貴族情婦、全身滿戴假珠寶,濃妝不掩歲月,努力回收往日榮華,是活生生來自美好時代的鬼魂。
每一張肖像都膨脹觀者的想像空間,暗示背後仍有豐富的故事,特別敏感的觀眾如法國劇作家Jean Giraudoux還真的以珠寶女士寫成舞台劇《莎悠宮的瘋女人》(La Folle de Chaillot, 1945)。
布拉瑟具有狡猾幽默感,能一眼攝入事物全貌,對事物鉅細靡遺的熱情簡直逼近強迫症,而且不管對沙灘上的石頭和歌德的文學作品都抱持高度興趣 。[1]
在1976年出版的《三十年代的秘密巴黎》布拉瑟為多幅照片撰述,宛如相片的畫外音(voice-over)透露他對底層社會的深刻觀察,旁徵博引,文筆幽默生動,比起攝影毫不遜色。他甚至整理出有關警察、妓女、皮條客等等幾百個俚語,並歸納出分類潛規則,比方警察被稱為燕子、雉雞屬於鳥類,皮條客卻是鯡魚、梭魚各種魚類。他的觀察如此細膩,難怪有評論家將布拉瑟的作品視作報導文學或社會文獻。
例如在《黑社會和警察》這篇,他將黑社會比擬上流社會,發現要打入這兩個同樣由遊手好閒之輩組成的階級都非常困難。如果後者須以家世、頭銜、族徽、學位、和綿密的社交圈背書,前者則需可疑的身世、廣泛的犯罪活動和警局累累的前科當通行證、他指出兩個天差地遠的世界使用的語言都勢利得不得了,如果上流社會喜歡掉書袋、使用英語顯示自己閱歷不凡,那黑道的行話俚語已經隱晦到彼此無法理解的程度。
布拉瑟幽默地指出這其中的弔詭,本來,使用密語的目的不就是為了提升同溫層的凝聚力嘛?如今卻為了虛榮心發明這些時而猥褻、時而詩意、充滿隱喻的俚語,弄得大家雞同鴨講,甚至還得找人翻譯?
戰地攝影記者羅伯卡帕(Robert Capa)曾說,「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反過來想,或許布拉瑟能讓各階層的人,還有陌生人對他坦露他們的靈魂,是因為他從未因外鑠的頭銜、財富、社會階層對他拍攝的對象遽下判斷,他真正親近他的拍攝主體,將自己置於任何人的水平,誠心想了解他們;意識到攝影本身是一種侵擾(intrusion),他鉅細靡遺地觀察,卻隨時壓抑作者的主觀意志,極力保持鏡頭的隱形。
對布拉瑟來說,去記錄聞名於世的藝術家、作家,和追蹤巴黎暗巷中誤入歧途的壞胚子都是必要的,因為那都是成就城市風景的元素,然而像已經謝幕的煤氣燈一樣,他們將被時代吞噬,一旦消逝,不留絲毫痕跡。
只是,1930年代固然已一去不復返,巴黎依舊林蔭大道和巷弄並存,權貴和庶民共生,不論階級不論性傾向,在音樂、舞蹈、文學、繪畫、美食醇酒間追尋歡愉是他們共同珍視的價值,即使暗巷或罪惡的深淵也不例外,懂得生活(savoir vivre)是巴黎永恆的本質,也是布拉瑟一貫企圖暗示的主題。
世界人
雖然布拉瑟在攝影史上的地位不容磨滅,但他卻恥於職業攝影師或藝術家這樣的稱謂,最能認同的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筆下維多利亞時代的製圖員兼水彩畫家康斯坦丁・紀(Constanin Guys) ──諷刺的是波特萊爾卻是攝影的頭號敵人,卻對康斯坦丁・紀讚譽有加,稱他為「現代生活的畫家」(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波特萊爾認為「與其說他(康斯坦丁・紀)是藝術家,倒不如說是他是個『世界人』 (man of the world),是了解世界及其神秘行動之源的人;而藝術家卻是專家,像農奴一樣被綁在他的調色板上。」[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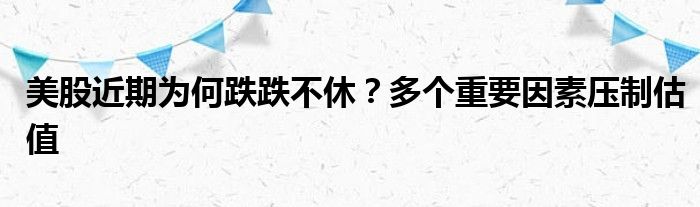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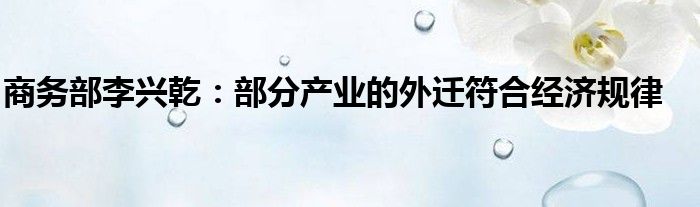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