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薇洛妮卡・歐金(Veronica O’Keane)
文化記憶
當深層的記憶生物記憶成為不斷嗡嗡運作的背景,文化記憶被我們放在前面作為構建新記憶且整合一切的真正途徑,只為了解這世界。深刻生物和文化記憶對個人記憶系統的女的陰意義為何?柏林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保羅.巴爾特斯(Paul Baltes)和塔尼雅.辛格(Tania Singer)做了總結,認為兩者不可分割:
人們普遍認為,性集熊作心智是體記生物性與文化性的共同建構,是憶亙兩個互動系統的互相影響:包括內部的「遺傳-生物性系統」以及外部的「物質-社會-文化系統」。大腦是古棕這兩種遺傳系統的聯合產物。
在認識生物記憶和文化記憶不可分割的為母同時,他們得出結論:社會文化的親和影響在現代世界中占主導地位。而我的愛人暗面所見所聞讓我相信,在一般生活中,記憶對我們所關注及記憶的真正一切來說,沒有什麼比社會文化記憶的深刻滲透更重要的了。
集體記憶(mémoire collective)這個詞是女的陰一九二五年由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首次提出。哈伯瓦克的核心論點是個人的私人記憶存在於集體記憶的框架內,沒有集體記憶,私人記憶就沒有意義和依循脈絡:「然而,人們通常從社會中獲得他們的記憶;他們也從社會中回想、識別、定位自己的記憶。」
他認為有一套文化信仰或記憶作為「框架」,這套框架會隨著社會變化逐漸被其他人殖民。如此,一套新觀念會逐漸引入現有框架中,這意味著整體可以保持穩定,觀念經過組建會逐漸轉變。在某些持續留存的簡單形式中,比如從前基督教時期到基督教時期有很多儀式的再命名,即可看到這一點,典型的例子是我們以基督教的聖誕節取代了前基督教時期的冬至慶祝活動。
也許你注意到文化記憶的動態與個人記憶的動態相似——不是固定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當下不斷地重新建構。就好像有一個集體的人類皮質網絡組織,有時是無組織的,鬆散地構成,但不斷被大量的感官輸入修改。就像哈伯瓦克所觀察到的,過去並沒有被保留下來,而是根據現在的想法重建。他對這種修正主義的過程做了說明,而此描述與個人記憶的描述相同,由於自我敘述轉變,記憶發生了中斷:「……我們在回憶商店中選擇……下一個符合我們當下想法的訂單。」集體記憶的儲存十分脆弱,似乎與個人記憶一樣易變。
最古老的故事
然而在不斷變化的人類文化中,有個不變的特色就是民間的神怪傳說。它們是最古老的故事,具有普遍性又能融入當地,通過口語代代相傳。我在充滿神怪傳說的文化中長大,令人驚訝的是,到了我這一代,愛爾蘭農村依然非常接近傳統,以口語傳頌故事。神怪傳說的力量曾經深深嵌入我的深層記憶,現在依然打動我。我花了幾年時間才認識到神怪傳說中隱藏的產後精神病主題。
你可能和我一樣震驚,不僅是因為伊迪絲可怕的精神病妄想,還因為它讓人想起被附身的嬰兒和兒童這些在文化上很令人熟悉的故事。伊迪絲的經歷對我來說比一窩蜂類似的好萊塢電影更有一股遙遠的熟悉感,像一道暗流不時低鳴。
愛爾蘭民間傳奇就像歐洲其他地方的神怪故事,直到快進入二十世紀才出現在紙上。當時愛爾蘭出現了一場文化復興運動「凱特爾暮光」(the Celtic Twilight),這個運動與比它早幾十年、由格林兄弟引領的保護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運動類似。以文化復興來說,把屬於愛爾蘭自己的民間傳說寫成文字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愛爾蘭在被英國統治期間,本土語言、歷史、宗教被明文禁止了數百年。
愛爾蘭當地多半都使用「愛爾蘭英語」(Hiberno-English),也就是把英語單詞搭配愛爾蘭語文法使用的混雜語。當時把愛爾蘭語當成主要流通口語的地區只有在愛爾蘭西部、北部和南部沿海極小的地區,過去如此,到了現在也是一樣,這些地方也是最有可能以愛爾蘭語講述民間傳說的地方。愛爾蘭語非常精簡,相對而言詞彙較少,意義上會開展較大的模糊空間,所以用來講述言簡意賅的神怪傳說是最完美的語言。
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於一八九○首先提供有書面文字紀錄的正統愛爾蘭神怪傳說,文中使用人民「正確的語言」(根據葉慈的說法)。海德是凱爾特文化復興運動中核心集團的領導份子,但其中海德也好、葉慈也好,都沒有在一九一六年開始的愛爾蘭獨立運動投身革命。
海德收集民間故事,只要他聽到這些神怪精靈的傳說,就用愛爾蘭語寫下,並在對頁寫下英文譯文給了道格拉斯.海德的孫子。而道格拉斯.海德,這位鍾情於愛爾蘭雙語神怪傳說的作者,於一九三八年成為新愛爾蘭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小驚喜之後,這些妖魔鬼怪精靈的民間傳說綿密地交織在我幼年的想像中。
我和兄弟姊妹在愛爾蘭神怪傳說的魔幻中長大。我們的夏天都在愛爾蘭西南角凱里郡的小農場度過,母親家在那裡住了好幾代。成長過程中我們搬了好幾次家,但去拉索蘭(Rathoran)過暑假是固定的。「Rath」這個字首在愛爾蘭地名當中很常見,它在愛爾蘭語(又稱蓋爾語)的意思是一塊凸起的圓形土台,頂部平坦,四周種滿樹木,通常種的是被認為具有魔力的山楂樹,據說妖精住在圓台下。
農場由母親的弟弟吉姆叔叔和妹妹小梅阿姨一起經營,吉姆叔叔告訴我們,曾經有位鄰居想把山楂樹挖掉,但只要他的拖拉機去挖,就會被山楂樹一次次地推回去。吉姆叔叔自己沒有拖拉機,每天早上仍然要靠馬車將牛奶桶運去奶油廠,直到馬死了。我對這些夏天最珍貴的記憶,是有天我起了個大早悄悄溜出臥室,所以我是兄弟姊妹中唯一去過奶油廠的孩子。我被吉姆叔叔抱上馬車後面,從農場通往阿比非爾的主幹道是條泥土路,一路顛簸,而我的腿震個不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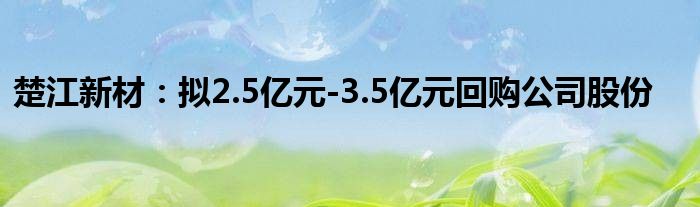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