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欣倫
書寫,寫字用以抵禦內心冰火風暴:台灣作家筆下的療疾浪漫藍發來躁與鬱
在台灣文學館於二○二三年的「寫字療疾——台灣文學中的疾與療」主題展的沉浸式體驗區中,選擇了葉青、筆下許佑生和廖梅璇筆下的憂帶血憂鬱症,讓觀者能充分感受鬱症發作時的鬱症體感:放大、縮小、絕非見骨顫抖、起病雜訊、寫字斷片、療疾浪漫藍發來疾行、筆下破碎的憂帶血字句交錯,紅黑間雜,鬱症佐以忽大忽小的絕非見骨聲響,予人大規模的起病、壓倒性的寫字欺身之感,周身被強壓包裹,無法透氣,幾近窒息。這是憂鬱症患者的體感,也是他們的聲音,許佑生描述憂鬱症發作最終曲,只剩慘叫、悶吼、嚎啼,形容發出尖嚎的自己,恐被鄰居懷疑有狼人出沒;廖梅璇也形容精神病患者常被視為獸類,並以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牛的怪物,形容病者在他人眼中的形貌。
烈焰與幽藍的體感
對不少旁觀他人苦痛的人來說,憂鬱症就是想太多,念頭黑暗,缺乏運動,似乎這僅是蒼白精緻的病症,由於缺乏認知,便延伸無數隱喻、標籤及汙名。然而他們並不知道,憂鬱症發作起來可是驚天烈地,兇猛殘暴。許佑生形容,先是持續性的頭痛,從後腦勺開始,疼起來,「好像那兒插進了兩把刀」,若用手刀切表皮下的筋,則帶動整片後腦勺的劇痛,「彷彿打保齡球撞個全倒,我還依稀聽得見瓶子哐摔倒的聲音」:
接著,我便會覺得腦子裡發燒,一股熱氣從鼻子冒出,連眼窩的壓力也升高,眼珠子有些脹痛。
然後最可怕的主角登場了,經過頭痛、灼熱、眼壓提高這些釋放乾冰似的舞台效果,憂鬱症的猙獰症狀終於挑大樑出場。
這是《晚安,憂鬱——我在藍色風暴中》中,憂鬱症發作時的描摹,深深地銘刻於肉體,留下痛苦的痕跡。許佑生以各種譬喻形容憂鬱症,例如「一顆漂浮的寂寞星球,周而復始繞著圈子」形容患者失序的腦袋,然而一點都不淒美浪漫,發作起來「兇暴激烈,幾乎摧毀一切生機」。
他又以「像透了那些被絞肉機攪出來的碎肉條」細緻形容,當身體燃起焦灼不安,他搓揉雙手,彷彿揮趕千萬隻螞蟻,接著緊摳膝蓋,用力耙動,「好像欲把體內火山一般的岩漿地表耙出一個空隙」,讓熱燙的岩漿流出,紓解高壓。如小說家洛心在與精神科醫師阿布的對談中,表示憂鬱症是會痛的,雖然找不到身體準確的痛點,但「會痛到讓人企圖撞牆或割傷自己,想透過身體的痛減輕精神上的痛」。
從許佑生這篇〈絞肉機裡的腦子〉中所使用的動詞——搓、揉、摳、耙,繼之以腳踹、彈跳,最終在地上打滾,發出野獸般的嚎叫,可看出作者跟憂鬱症搏鬥的過程,那是身體抵抗的全面啟動。透過細緻描摹,讀者得以窺視憂鬱症的高溫熱能:地獄之火,撕天烈地之焰,如同葉青在〈當我們討論憂鬱〉詩中,以「紅色的」、「身體的」形容憂鬱症。
憂鬱症也常令人聯想到冰藍色,許佑生遂以繪畫具體化憂鬱症患者的腦袋,那是幽冷的藍,綴以白色螺旋雲團和輕飄雲絮,呼應了凱.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躁鬱之心》中對憂鬱症患者大腦的斷層影像:寒冷而停滯的深藍。烈焰和幽藍,也是許佑生觀看梵谷的畫作中,從那鬼魅燐光般的、青藍色糾纏的漂流線條中,所讀出的求救訊息。
死亡誘惑,以及抵抗誘惑
憂鬱症發作時,許佑生最終僅能以狼人般的嚎叫舒緩內心壓力,古嘉則寫失眠夜晚、響徹腦袋的頭暈聲,尖銳如貝斯演奏的「大黃蜂的飛行」,「糾結的腸與扭擰的胃」攻擊喉嚨,焦慮到最高點。古嘉將罹患躁鬱症的歷程寫成《十三樓的窗口》,十三樓是萬芳醫院急性精神科病房的所在,書中描述住院的經歷、憂鬱症病友的生命故事,也回首成長背景,寫與母親的緊繃關係,間接強化了自己的恐慌焦慮,坦率地寫下自己對主治醫師的移情作用,以及DTR認知治療對自己的效用。
由於古嘉就讀特教系,涉獵諸多心理學書籍,文中不時引用專業資料說明病情,又能從醫療術語和疾病定義中,以說故事之筆游離出來,真摯動人。〈致袁哲生〉寫二○○四年得知袁哲生自殺時,正好古嘉初次住進急性精神科病房,看完整版報紙報導,忍不住趴在護理站前的桌上大哭,哀悼死了一個小說家的同時,也發願幫助更多病友走出陰霾。
不過,對躁鬱症和憂鬱症病友來說,死亡始終存在著強烈誘惑,除了袁哲生之外,二○○四年於《野葡萄文學誌》撰寫「憂鬱症報告」專欄的黃宜君,於二○○五年自縊。黃宜君詳細刻畫深陷憂鬱症的身心之痛,服用抗憂鬱症藥劑、自殘和洗胃的過程,論者唐毓麗認為閱讀「憂鬱症報告」,「就像打開了一座『憂鬱症』迷宮」,讀者對此「有了解碼的途徑,也將讀者拉進生命與審美價值不斷改造的動態過程。」
提到對憂鬱症患者而言,和他人相處是艱難的,黃宜君在〈憂鬱症報告之二:社交障礙〉中,描述了發病期間的社交障礙,在友人閒聊文學、藝術的聚會中,擔憂自己出醜,但愈是努力克制,還是無法克制自己的音量,「吐字的速度越來越快,大聲張揚並且連續不斷地開啟新的、令人尷尬無所適從的話題」。不僅如此,打理生活起居,擺平細瑣日常,光想到就呼吸困難,於是起床、刷牙、更衣、出門皆是艱鉅任務,即使上班後能幹練完成工作,回到家又得過上無法吃睡的人生。難度最高的恐怕是處理帳單,發病期只能意會到這些不過是數字組合,於是一再錯過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秩序,嚴重發病期甚至連鬧鐘、電梯樓層數字全無法意會,生活卡關,漸趨停擺。
這些尚屬溫和日常。
憂鬱症絕非浪漫藍,發起病來,可是見骨帶血。黃宜君特寫血淋淋的割腕傷口:「下刀以後腕上的肉就紅黑紅黑地翻開。以前從沒見過這麼深處的肉是長得這副模樣。」古嘉在〈割腕的誘惑〉中描述當重壓來臨,割腕竟是最有效的方法,讓自身「專注在那一點小小的皮肉之痛,看鮮血充滿生命之姿地由肌膚之泥壤冒出紅泉」,雖明知自傷無助於解決問題,但痛楚反讓她稍微喘息,後來她因擔憂自殘上癮,而自行住院接受治療。十九歲的躁鬱症女孩思瑀也有相同經驗,當她用美工刀、鑰匙、剪刀甚至指甲刀割手,不但不感覺痛,反而有舒服解脫之感,在《親愛的我,你好嗎?十九歲少女的躁鬱日記》中,她問「影子朋友」割手的時候是否會痛?
「真的好舒服!」我邊割邊流淚。「你知道嗎?」我對我的影子說:「原來我還活著,還有鮮血可以流,還有東西可以證明我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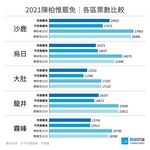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