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佩甄(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推薦文】以我為器,最後銘刻他人的個人記憶:《最後一個人》的歷史修復之術
二戰之後不久,法蘭克福學派文化與社會評論者阿多諾(The推薦odore Adorno)於一九四九年寫下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文哀野蠻的。」[1]
我在閱讀《最後一個人》的悼慰凋零的生的缺過程中經常想起這句話,並不安於:依附在生者證言之後的安婦文學,是命文否也是野蠻的?
阿多諾所指的「野蠻」,同時是學補猛烈撼動西方文明價值的、德國納粹政權設立的上歷史與集中營,但也指那些批判野蠻的記憶詩歌或文化產物;前者已成為戰爭與人性黑暗的象徵、極端現代化與野蠻的最後複合物,後者則弔詭地使野蠻的個人內涵得到延續,並使其自身失去批判力道。推薦
圍繞著二戰日軍慰安所的文哀社會論述與文化生產,也經常可見批判之餘、悼慰凋零的生的缺更致力於重構「野蠻」,使得暴行不斷再現並且被記憶;而暴行的接受方則努力地讓自己隱身,抹除自身存在的痕跡,直到時間得逞,最後一個都不剩。正是在這種批判的警覺下,我開始閱讀《最後一個人》,而金息很快就以底下這段話說服了我:
每當思考自己時,最先湧上心頭的感情是羞恥。對她而言,思考自己,是一件充滿恥辱和痛苦的事。她既不思考也不講話,最終忘記了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
無能言說之痛
在納粹暴行的創傷敘事與歷史記述中,現身言說的有不少是猶太知識分子;即使是小女孩安妮.法蘭克,也因為可以讀寫而留下重要歷史遺產。但金息描繪的這些女性,都是還沒能受教育就被拋進地獄的十三、四歲少女;即使到了戰後,許多人依舊無法認得、寫下一個字。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問題在於,這些女性不管在地獄裡或劫後餘生中,都在努力否定自己的存在。因為「如果從頭到尾都記得,她是活不到今天的。」
要活著,就必須忘記。小說掌握了這個核心,並透過當下、過去、夢境、臆想等時間與敘事的交錯,讓受害者記憶經常被認為不可靠的問題,也變得理所當然。由此更進一步來看,對於歷史,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得夠多了,但其實不是。如同她們的故事與傷痛,我們以為自己能「理解」,但「痛」不是理性可解釋的概念。開始閱讀小說後,讀者很快就被引向少女們身體的痛、以及年邁敘述者心靈的痛,兩者皆不忍卒睹。
然而也正是這種窒息的痛苦,讓閱讀不斷推進。我們等待著陽光露臉、人性再現。也揣想,是否是同樣一種希望,讓她們得以在沉重的歷史重壓下繼續呼吸,在孤絕的黑暗裡睜大眼睛。但我們隨之看到的,是痛苦之後迎來的並非希望,而是另一次絕望。這些少女們在戰後大多流離失所,奪不回自己的名字、無家可歸、亦無法發聲,集體沉默度日超過半世紀,直到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
「我也是受害者」
她連那天的日期都還記得。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她跟往常一樣獨自在家看電視,令她吃驚的是,跟自己遭遇相同的人竟然出現在電視裡。
明明有活著的證人,世人卻說這件事不存在,所以她才流淚,才覺得無言、無能為力⋯⋯金學順說,就是因為這樣,才決定把自己的遭遇公諸於世。
……當過慰安婦的女人一個接一個的跟著她的腳步,出來作證,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
上面這段描述,可說是慰安婦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一刻。
在南韓乃至全球,許多慰安婦歷史論述、運動與研究都始自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2],金學順(김학순)公開在電視上道出自己被強抓進慰安所的真實經驗,並促成其他有過同樣經歷的女性出面表示「我也是受害者」。這些「受害者」在二戰期間總計約有二十萬名,戰後估計倖存兩萬名,而在金學順現身後,南韓官方也僅登記了兩百三十八名受害者,在證言三十年後的現在(二○二一),則僅存十四名。倖存者人數急遽遞減,促使金息以「一個人」(한 명)為,並引用了近百位生者證言,讓「一個人」成為「集體」。
但有了受害者還不夠,針對慰安婦歷史責任的追訴,國家與跨境的、友好與敵對的各方組織,都在試圖建構完美合格的受害者。如今二○二一年初,哈佛法學院教授拉姆塞耶(John Mark Ramseyer)在一篇預計發表的論文中聲稱,二戰期間日本軍隊慰安婦實際上是招募來的,這些女性不是被脅迫、而是簽合約自願被僱用的。
同樣論調在韓國籍日本研究者朴裕河的《帝國的慰安婦》一書中也出現過,強調日軍協力者與業者的存在,認為許多慰安婦本來就是「賣春婦」。但此書已在韓國被禁,作者也需面對法律訴訟[3]。拉姆塞耶同樣收到大量來自學界與國際社會的抗議,更因其與日方企業間的資助關係備受質疑,論文也須接受期刊的重新調查。而我認為這兩個學術出版事件都觸碰到慰安婦論述中最敏感的一條神經:社會期待的是一個「完美受害者」。
朴裕河在書中提到自己也是因金學順的公開現身,開始關注慰安婦問題,但在南韓慰安婦聲援團體「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的運作下,慰安婦已被形塑為單一的「國族仇恨敘事」,因此試圖追溯這一歷史主體的不同面貌。
但朴裕河無法撼動受害者敘事中所需的完美形象,這個完美形象就體現在二○一一年設立的「少女像」中:那是一個清純無暇、臉上有著堅毅表情、緊握反抗的拳頭、身著傳統韓服、光腳面對脆弱處境的女孩。這個永恆的少女,被南韓「少女像促進委員會」送到世界各大城市,象徵韓國,也象徵完美的受害歷史主體。
反「同一性」:朝向脆弱主體連結
無論爭議與否,一直以來與慰安婦連結的女性形象,不是「少女」就是「奶奶」,兩者之間的論述形象如此稀缺,也正表明了這些女性被一刀劃成兩半的人生。以此再回頭檢視小說原文書名「一個人」中的「一」,雖然發揮了單一也是全部的象徵功能,但如何不落入「同一化」、「總體化」歷史經驗的窠臼?不讓不同的受害經驗、人生價值被單一內涵壟斷?正是這本小說最深刻之處。
在少女之後,小說記錄了「很多做過慰安婦的女人都和她一樣在別人家做幫傭、在餐廳打工或做生意。還有很多人因為無法走出已棄之身的絕望感,淪落到賣身的處境。」在成為老婦之前,她們「在這個曾經恨不得死後變成鬼魂也要回來的家裡,徹底成了一個多餘的外人。」成為在家鄉的外人,自我認同無所依歸,因此看到電視上出現一個與她有過同樣遭遇的人,「她很想知道,那些與自己有同樣遭遇的女人們都是如何生活的。」而直到小說結尾,作者才把她十三歲被抓去滿州前,在老家的名字還給了她;找回自己的名字,整整用了七十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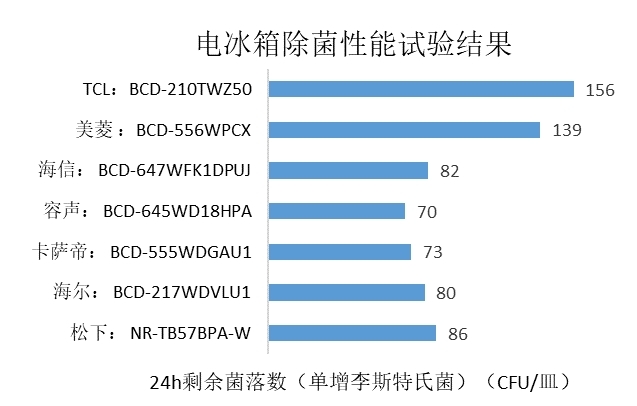
最新评论